周大伟:为什么是美国?
周大伟本文系作者为《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中国大陆版撰写的译者序言
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1832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和他的朋友博蒙乘船从法国港口勒哈启程,前往他们一直充满好奇的美利坚合众国。对这次漫长的游历,托克维尔曾对人们解释说:"我们不是要看大城市和美丽的河流,我们是想尽可能细致而科学地考察庞大的美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对此,每个人都在谈论,每个人却都不清楚。"
有趣的是,就在数十几年前,由于启蒙运动的举世瞩目以及启蒙思想的深入人心,托克维尔自己的祖国--法国,曾经是全世界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1743-1826)就曾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
然而,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的法国人则有苦难言,他们对这类恭维辞令似乎并不感激。在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硝烟散去之后,他们怃然发现,远在大西洋的另一侧,"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似乎已经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这场革命的实现显得很简易;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直接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的移民,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并把它单独移植到新大陆。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影响民情的过程中和平地确立了法律的性质。"(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4页)
这个以所谓"简易方式"就收到了"革命的成果"的国家,当然指的就是美国。结束了在美国9个月的游历之后,托克维尔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美国的民主》。经过对另一个大陆的考察,托克维尔更加深信,贵族专制制度必然衰落,平等与民主的发展是"那么广泛而且势不可挡"。而且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如果我们今天确有必要将民主和法治视为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知识(或制度)体系的话,那么,在大约两百年前的欧美国家,这种区分或许并没有今天那么鲜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托克维尔在美国期间,不仅仅考察了"美国的民主",而且更多的是考察了"美国的法治"。
当托克维尔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美国"后来居上"的原因。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美国经验的巨大张力和定力。他写到:"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也会像美国人一样,达到身份的几乎完全平等。但我并不能由此断言,我们有朝一日也会根据同样的社会情况必然得到美国人所取得的政治结果。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但是,产生法制和民情的原因在两国既然相同,那么弄清这个原因在每个国家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所在。"(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英文版原著上卷绪论部分)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及托克维尔这个人,并不仅仅因为他撰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的民主》这类名著,而是受到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暗示,希望通过细致地理解美国社会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部分。
其实,在美国历史学家们看来,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还正处于青葱幼稚的艰辛岁月。美国法制真正成熟的年代,其实还是在刚刚远去不久的二十世纪。如果我们不对二十世纪的美国法律发展史做出一个细致的观察,恐怕很难理解这个国家成长壮大的密码所在。
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教授Gregory Clark教授曾在他的量化历史研究成果中指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很有趣,但并不关键。"从宏观上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按照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
同样按照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50美元(与西欧诸国大致相似),在晚清洋务运动发端时也不过仅仅是530美元。即便这个数字表明"中国古代GDP曾在世界领先",也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意义。整个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几千年中,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其实变化甚微;因此,无论经历多少次改朝换代的血与火的考验,其中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并没有发生多少本质性的变革。因此,我们几乎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如今充斥于电视机屏幕里那些多如牛毛的中国古代宫廷戏剧中,同类型的人物和剧情居然可以在清朝之前的各个朝代里尽情穿越而不会令人产生质疑。因为,在收入与生活方式处于静态不变的状况下,剧情中的那些朝代到底叫"汉朝"、"隋朝"、"唐朝"、"宋朝",还是"元朝"、"明朝"或"清朝",已经意义不大,至少没有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么大。
即便中国古代GDP曾在世界领先,也没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科学技术史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类已经有几千年的生活历史。但是迄今为止这个地球上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事物,都是在过去的100年中出现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出现的。甚至于今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竟然是在最近五年内出现的。你不妨稍微想象一下,五年前的今天--史蒂夫·乔布斯还活在人世,iphone4s 还没有来得及问世;五年前的今天--诺基亚公司还占领着移动通信设备40%的世界市场;五年前的今天--QQ在中国大陆还风靡一时,腾讯公司还正在运筹着如何把源自美国硅谷的kakao Talks技术移植成本土的微信(WeChat)。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在他这部堪称研究美国近现代法律史的里程碑著作《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各种诉讼,主要与工业革命引发的科技进步有关。他感叹到:"今天,人们提出的各种诉讼,在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 。
20世纪是人类公认的巨大变化时期,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过去的整个二十世纪中,美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的判例一直在重塑着宪法,浩如烟海的司法判例和成文法规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各行各业;上百万律师们涌动在这个国家的城乡内外、大街小巷。然而,稍微细心一些的人会发现,这个国家宪政的基本骨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并没有动摇过--不变的合众国联邦共和制、不变的九人最高法院、不变的两党轮替执政。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甚至是性革命都曾呼啸而过,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在美国发生。用本书作者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的话说:美国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在变化过程中发生的稳定性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新酒不断倒入了旧瓶里的故事。
由此,令人想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充满魅力的一个词语:"超稳定系统"。今天,用它来形容美国的制度建设,或许更为贴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名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大胆地将系统论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从中国皇权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 应当承认,上述假说对于理解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发展脉络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无数证据表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其实是一个从农耕文明变成工业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乡村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的过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还大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很多人尽管穿上了舒适合身的西装,满口都是现代世界的新颖词语,但思维方式并没有远离农耕文明的影响,传统的深层结构其实一直在左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可以理解为这种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依照某种惯性运行的行为模式。例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不少内忧外患都和帝王身边的宦官太监的恶行相关。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皇帝还总是离不开这些身边的宦官太监们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样一个不透明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循环系统中,除了身边这些人以外,皇帝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以信任的人。结果,从秦朝的赵高到清宫里的小李子,从"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到"一把手"身边的大总管,一个个龙种最后都变成了跳蚤。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故事也是一个新酒不断倒入了旧瓶里的故事。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国的故事却是一个在变化过程中发生的动荡不安的故事。从宏观上说,这类持续的动荡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世界对传统农业世界的征服,来源于一个主流文明对一个衰落文明的挑战,而在现实社会层面则体现为接连不断的列强入侵、内部战争乃至改朝换代(据历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3700次战争,大部分都是内战)。这一切,似乎来自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往往与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无关。
不少人都乐于嘲讽"美国的年轻--历史短暂、文化浅薄",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这么自嘲不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进行历史性的思考,马上就会发现令人惊讶的结论。其实,今天的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一脉相承,难以分割,美国文化可以被认为是欧洲文化在美洲大陆上的延伸。当17世纪初期英国异教徒来到美洲大陆时,几乎带来了所有的欧陆文明,诸如学院、医院以及法院。美国文化也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就像从东方的中国移民来到美洲大陆一样,最早期的美国移民是地地道道的欧洲人。海外华人移居美国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只是很少有人会说,这些中国人文化历史过于暂短,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往往会无比自豪地争辩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既然中国人、印度人可以这样说,
当你听到美国的欧洲后裔们也这么说,难道就很奇怪吗?所以,如果把今天的中国与所有之前的历史无限延伸,不妨称其为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同样,难道美国就不应该和300年前的欧洲、尤其英国的历史关联起来吗?
即使我们以为美国的历史可以从17世纪以后算起,也不足以妄议这个国家的"历史短暂和文化浅薄"。平心而论,美国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政制度。仅此而言,美国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拥有最古老的民主和联邦制,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也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比如民主党)。
如今,不少人都在谈论"美国衰退论"。其实,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迅速发展后,美国进步的速度的确放慢了很多。但是,这个国家在知识、财富和经验方面仍然在不停地积累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处在某种"进步的运动"之中。只是和有些新兴国家相比较,显得进步放缓并且相互距离显得缩短而已。1998年,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谈论美国时曾经说过,或许恰恰因为全球化加快了步伐,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却是无法忽视的力量。如果说托马斯·杰佛逊(1743-1826)就曾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那么,今天的世界上,每个人也大致都有两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和美国。美国的文化在这个地球上几乎无所不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关注着美国政治家们的一举一动,以至于每个人的脑海里仿佛都存在着一个虚拟的美国,大家都在参与和思考美国的文化、政策和法律的变化--无论人们是否情愿,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感觉自己成了美国公民。(参见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一书第12章)
理解美国的社会,必须要了解美国社会的核心部分--美国的法治以及美国法治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稳定的法治基石是如何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不宣的中流砥柱?为什么美国的法治能够相对稳定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成为一些对外输出的"美国产品"?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劳伦斯·弗里德曼教的《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一书,大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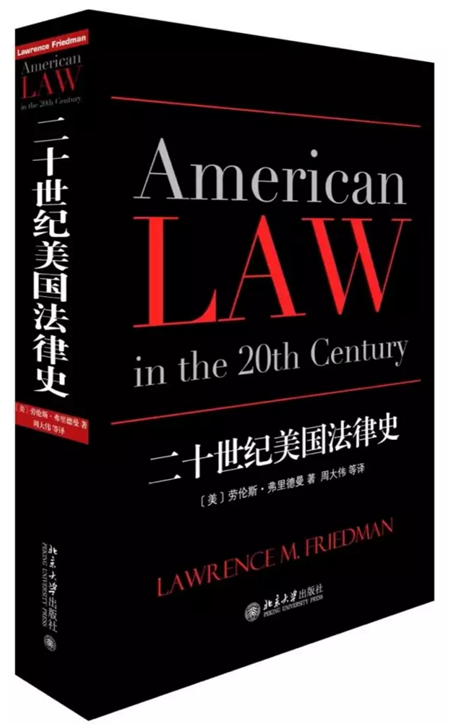
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和他的《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一书的英文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于2002年在美国纽黑文市和英国伦敦市同时出版问世。
此书作者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 194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195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获法律博士学位;1951年至1956年在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任教;1956年至197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任教;1978年至今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同时担任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法律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for Legal History)会长、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会长。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
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是二十世纪美国"法与社会"学术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法律与社会关系、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财产法学、契约法、信托法和福利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并在世界法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被誉为美国法社会学界、法制史学界以及比较法文化论的泰斗。
在二十世纪世界法学研究领域,曾经有两种堪称革命性的法学研究范式,一种是"法律与经济"研究范式;另一种是"法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两者都引发了世界法学研究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法学研究中的两道靓丽风景。
弗里德曼教授是"法与社会运动"主要领袖人物,是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研究界的世界级著名学者。他运用法社会学的方法论,对法律史、法与社会变动、法与社会科学、法律文化、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财产法学、契约法、信托法和福利法以及其他法学实务问题作了广泛、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他的专著《法律制度: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1975)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与麦考利(Stewart Macauley)共同编著的《法与行为科学》则是战后美国法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好的入门指南。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一书是其代表作《美国法律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作者用他一贯的优美流畅、深入浅出的文字,引导读者进入美国近现代法律史的殿堂。如果有人试图了解近现代美国法律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全球化法律的影响,此书堪称最佳作品。
本书除了在纵向的美国法律发展史上,利用著名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叙述之外,还在横向的社会发展层面上,叙述了美国法律在不同阶段与经济、科技、社会和人文诸方面的逻辑互动。弗里德曼教授首先讨论了一个与法律的独立性有关的核心问题:法律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它是否只能随着其自身的规则和内在的程序亦步亦趋地成长和衰败呢?还是法律制度又是整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旦世界发生改变,法律也必然改变呢?读者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会明显地发现弗里德曼个人的见解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这个取向和态度,几乎浸透在他写作本书的方式里。
弗里德曼在《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中将1900年美国的社会和法律和2000年美国的社会和法律进行比较,他把二十世纪分成三个主要的阶段:
1、二次大战前的旧秩序;
2、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法治的延续状态;
3、现在的生活方式。
每个阶段的叙述中都穿插了宪法的体系变迁、政府的结构变化、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法律职业化的积累以及法律文化的变迁等等。他认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发展转折点。从那时起到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无论从那个方面看,都已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改变。民权的兴起、死刑的慎用、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的保护、贸易国际化、法律的全球化等等,本书不断在向人们暗示,以法律现实主义运动为代表的美国法律思想以及美国法律改革运动,其实一直在充当着整个世界法律文明的助推器。
在本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弗里德曼并不完全是美国现行体制的歌颂者,他对美国法律制度中的诸多弊端持有尖刻的批评。因而,不少人可能会以书中的只言片语来判定他可能是个有左翼倾向的学者(如同一些另类的犹太裔美国学者那样)。其实,要真正理解这种批评,我们必须回到美国社会的现场。对政府的方方面面进行责备和抱怨,而不是对自己的政府取得的一些成果夸夸其谈,这恰恰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本性使然。因为,民主-法治社会的首要特征,就是国民监督政府及其人员。如果包括学者在内的国民为政府大唱颂歌,那是倒是非民主-法治社会的性格。在有些国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往往被视为"右派",而在欧美国家的此类知识分子却被视为"左派"。其中的奥秘,显然皆出于他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
其实,弗里德曼教授对市场经济环境中法治社会的认可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执着地认为,不论这个世界走向何方,一个清楚稳固的事实是:法律和法的运用将一直存在。在社会的每一面,不论高级或低级,所有的冲突、争执、妥协、和解、变动,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是受法律所驾驭的。即使像日本这种声称自己是个例外的国度,其实也是如此。不管其中存有什么差异,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透过法律来管理其社会--所有非规范方式得让位给规范方式,--所有的习惯被法律所替代,--陈旧传统的观念会逐渐消融。我们将看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整个法律史之迷,或许最难解的就是如何把众说纷纭的言说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事实加以有效隔离和区分。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官方所推崇的法律神话、媒体中夺人耳目的法律故事与真实生活中的法律实施,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尽力避免主观偏见并且冷静客观地对社会现象做出判断,绝非易事,有时甚至需要力排众议的勇气。例如,近二十年来,美国律师的数量增长惊人,律师的形象变得极为负面。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想迎合大众的通俗看法,似乎易如反掌。然而,弗里德曼教授却极为冷静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在本书中写到:"许多人,甚至经济学家,都认为律师是吸血鬼,是伤害经济的趁火打劫者。律师确实不是天使,但是反对他们的一般案例,大多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有些律师的确提起过无根据的诉讼,有些律师欺骗过他们的委托人,也有些以挑起纠纷为生。然而究竟有多少人这么做了,则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也很难说,到底诉讼的麻烦是否伤害了经济。当然,我们可以径直用金钱来衡量一场诉讼的代价。麻烦在于,律师提起诉讼带来的好处,是很难用金钱来换算的。如果一家大公司打输了一场性别歧视的诉讼,我们可以合计一下罚金和律师费等等,但是我们如何如赋予这一官司胜诉所得到的价值呢?律师惊人的数量及他们衣食无忧的事实(有些律师可以挣到数百万美金)--意味着他们在发挥着某些功能;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忍受百万只无用的吸血鬼。
事实是,法律制度如此复杂、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律师成为绝对必要的。遭遇麻烦的人显然需要律师。其他人则需要律师以避开麻烦。企业需要律师为他们处理政府的规定。事实上,罗纳德·吉尔森(Ronald Gilson)曾经主张,商业律师能增加价值,通过扮演"交易成本工程师的角色,'让整块大饼变大'"。(见原著英文版第470页)
在弗里德曼教授这本书以外的其他文章里,我们庆幸地看到过他对中国的法治的评论。他指出,有人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并不仅仅指的是中国大陆,还包括超出中国国界以外使用汉语和拥有中国文化的地域。倘若果真如此,这将不是一个儒教的中国,而是一个科技发明和进步的中国,贸易发展和市场开放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将别无选择地借鉴美国法律中的经验。至少在一个关键点上没有悬念:那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大国意识和历史悲情的国家而言,很多人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承认,过去一百年里在欧美国家发生的种种法律路径和故事,会在自己的国家里亦步亦趋地重演。为了避免误导人们滋生对美国法律霸权意识的误解,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似乎在小心翼翼地叙说美国法律路径的普适性。他在《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这本书的结尾部分语气平和地写道:"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我们究竟要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世界改变,那么这个世界的法律也会改变。……法律事务就许多方面而言,依旧是非常地域性的东西。大部分律师都是地域性的。然而,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全球化的法律。有些事情看来正在渐渐酝酿成熟。如果文化和贸易正在全球化,那么,法律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效仿"。
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几点感悟
早在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Foster City 公共图书馆里借阅到《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这本书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想把它翻译为给中国读者的内心冲动。后来,我有幸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与弗里德曼教授相识。无论是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他那间到处堆满了书刊的办公室里,还是在Pola Alto市的University Avenue上那间温馨的"大学咖啡馆"(University Cafe)里,我曾经和弗里德曼教授相约面谈,多次近距离地感受他本人大师的风范;回忆起来,这一切都当属于自己生命中最幸运的际遇之一。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法律发展史,劳伦斯. 弗里德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弗里德曼教授是美国有史以来个人著作被引用最多的法律学者之一。他本人被公认为研究美国法律史的最重要的学者,并且是上个世纪末以来法律社会学中"法律与社会运动"(Law and Society Movement)的核心倡导者。在过去的时光中,他至少写过近二十本法律专著,发表过两百篇以上的长篇学术论文。他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被翻译成十种以上的文字。他告诉我说,中国的文化让他深感奇妙。他的终身遗憾之一,就是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风趣地写到:"那些可以记住5000个字符(而不是26个字母)的人们,真让我惊叹和着迷。"
弗里德曼教授曾在交谈中告诉我说,他不嗜烟酒,晚年开始喜欢喝茶;他不打高尔夫球,对外出旅游也兴致不高;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甚至早年还写过几部与谋杀案有关的侦探小说。如今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几乎每年还能写作出版一本法学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
弗里德曼教授在学术上的取得的巨大成功,似乎对新一代年轻学者们频频发出暗示:如果你打算终生投身学术研究,看来首先要做好当一个经典"宅男"的准备。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大陆工作和旅行过程中,常常有不少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前来向我咨询有关子女如何学习外语和如何赴欧美国家留学的事情,其中不乏很多各级各类的政府高级官员。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些人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常常充满着爱恨交织的暧昧;但是我更相信,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的爱,毫无疑问是真挚和深沉的。我试图认真地告诉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我们无法预知过于久远的未来),除非个别的原因,我建议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最好选择学习英语并且最好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今天这个地球上几乎80%以上的新知识都最早出现在英文文献之中,而且它们也最早出现在美国这个充满创造力的国家。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进步,希望青年一代学有所成,就应当鼓励他们到新知识的最前沿去深造和探索。
在撰写这篇译者序言的时候,我清晰地意识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的经济体。只要这个庞大的国家不像其东北角那个奇怪荒诞的邻居那样封闭起来,它在与当代世界的接轨过程中,就一定会取得不断的进步。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从洛杉矶飞至上海,其实不过是在飞机上打个瞌睡、吃两餐饭和看两部电影的时间;如今,每天都有上万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两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每年,有数万名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更有二十多万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据统计,其中的70%以上都将学成回国)--这几乎比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留学生的总数(包括他们的家属)还要多;而且,在这些留学生中,攻读法律学科的留学生一直在逐年递增。如果弗里德曼教授这本名著能够为海内外众多的法律研习者提供有益的帮助,我将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