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思维在刑法学上的壮阔前景——简评杜宇教授的《类型思维与刑法方法》
刘仁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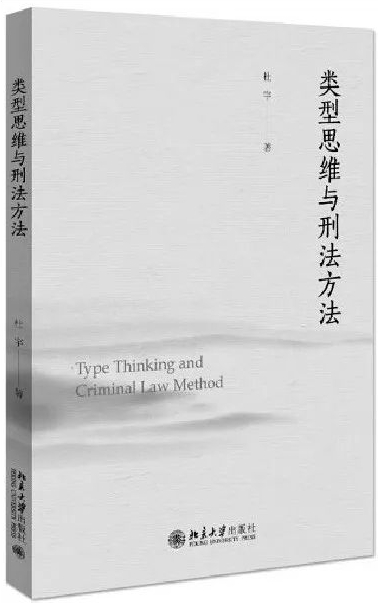
著作者:杜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复旦大学杜宇教授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研究刑法学中的类型思维,近二十年间相继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重要法学期刊上就此发表一系列成果,推进了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近日收到他寄来的《类型思维与刑法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立即翻阅,深感此前微信刷屏中有专家称此书为“二十年磨一剑”所言不虚。作为多年积累而成的学术结晶,该书对类型思维的特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领域中类型思维的应用、类型思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进一步巩固了杜宇教授在该领域的学术标签地位。
本文以贯穿全书的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对比为核心,谈点阅读心得。
关于类型思维的特质。作为刑法学者,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较习惯和擅长的是概念思维;在概念思维方法的指引下,我们在语词文义的严格限制中追寻刑法规范的确切涵义,并竭力在不同的概念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概念思维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应看到,其带有一定的僵化性和封闭性,完全依赖它难以适应鲜活开放的现实生活。也因此,许多时候基于概念思维的刑法讨论常常在无休止的学术争论中见仁见智、无果而终。正是针对概念思维的此种缺陷,类型思维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在与概念思维的对比中,本书归纳出类型思维的几大特质:结构性、层级性、意义性、开放性、中等抽象性。[1]
在探讨类型思维特质的过程中,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作者没有为了凸显自身学术主张的新颖性而过度强调类型思维的独特性(而这正是拉德布鲁赫等传统类型论学者热衷强调的内容),而是立足于类型思维的视角,发现了类型与概念之间相互补充乃至循环运动的可能性。例如,书中指出:一方面,类型与概念相互补充,脱离类型的概念将陷入抽象与空洞,而失去概念的类型将失去目的与方向;另一方面,类型与概念处于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立法活动将经验类型抽象为规范概念,而司法工作将规范概念开放为生活类型。[2]这确实是准确把握和生动表述了类型思维与概念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熟悉传统概念思维的读者有效理解类型思维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类型思维在刑法领域的应用。“类型思维在法学上的发迹,完全应归功于刑法学的发现”,[3]遗憾的是,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忽视了对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类型思维资源的发掘和整理。本书作者以刑法学中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为线索,梳理出构成要件从行为类型到违法类型再到责任类型的演进脉络,并通过我国实定刑法文本的抽样分析证实了刑法构成要件中类型范畴存在的广泛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指出,类型思维可在刑法学上进行全面推展,即可从构成要件扩展到犯罪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从行为层面发展到行为人层面,从犯罪成立体系延伸到刑事法律效果体系,最终全面推进至刑法学的整个版图。这无疑让我们看到了类型思维在刑法学上的壮阔前景。[4]
在细致梳理刑法学术史上的类型思维观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中应用类型思维方法的具体思路。在立法领域,具体规范的形成应当是法律价值与生活事实之间的相互调适,最终形成处于当为与实存、抽象与具体之中点的“规范类型”的过程;[5]而在司法领域,本书倡导“合类型性解释”方法,强调法律解释必须以类型为指导观念,解释者应当努力探求实定法背后的类型基础,通过案件类型比较的方式探索规范类型的轮廓与边界。[6]总之,司法适用中抽象的刑法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间的彼此嵌入,绝非通过简单的概念涵摄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在类型思维的指导下,经历复杂的归类、诠释与价值判断过程才能最终达成。
对类型思维尤其是“合类型性解释”方法在刑法实践中的应用,我也曾有过尝试和体会。以我研究过的“恶势力犯罪”的司法认定为例,“恶势力”本身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普通犯罪团伙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界限,而只有“或多或少”的区别。因此,我们的研究指出,类型思维对司法机关认定恶势力能有所助益,具体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探求法律规范中作为类型的“恶势力”的主导形象,以此为基准比较个案中的对应要素是否达到与主导形象相匹配的程度,最终得出实质合理的结论。[7]
关于类型思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领域不容撼动的基本原则,任何刑法理论与方法都只有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正当性。在刑法领域倡导类型思维方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就是来自罪刑法定原则(尤其是作为其重要内容的禁止类推和明确性原则)的质疑。
针对“禁止类推”原则的质疑,作者大胆对该原则的可行性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解释和类推之间根本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即便广受认可的“可能的文义范围”标准也无法承担区分两者的重任;此外,通过考察四类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当然解释),作者发现类推思维其实蕴含其中、无法分离。据此,作者认为,作为思维方法的类推在刑法领域实际上无法禁绝,只能为类推设定合理的标准。针对“明确性”原则的质疑,作者从刑法规范的有限明确性和适度模糊的必要性两个角度,论证了带有开放性和模糊性的类型思维不仅能够满足刑法体系的需要,而且还更加有利于实质正义在刑法实践中的实现。
对类型思维和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上述论证,深化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在动态中前进和发展的理论:作为实质侧面的明确性原则和适正性原则[8]的发现,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完善的明证。在传统的概念思维指导下,刑法规范被视为由诸多概念组成的封闭体系;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就是要维持这些概念边界的稳定性与清晰性,以此来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隐藏于刑法解释背后的类型思维的剖析,指出了简单的“禁止类推”原则和绝对的“明确性”原则的局限性,为刑法学界反思罪刑法定原则可能的限度,打破建立在概念思维基础上对形式理性的迷信,进而为更加合理地处理法律安定性与妥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本书较好地阐释了类型思维的思维特质、适用方法和正当性基础,为破除概念思维的“神话”,寻求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间的有效沟通方式,在立法和司法领域调和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潜在冲突提供了洞见与启发。同时,本书也在相当意义上打破了概念思维在刑法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使长久以来被遮蔽的类型思维的价值得以释放,亦使得概念思维与类型思维成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思考方法,这与我一直倡导刑法学研究方法应当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立体刑法学理念是相通的。当然,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新颖性和复杂性,本书的某些观点和论证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之间的界限,虽然现有方案均难以提供满意的答案,但本书的论述和思路是否足够深入和清晰,至少在我看来也还不能彻底解渴。甚至在一些域外移植过来的术语表达方面,如何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改造,作为优秀的青年刑法学人,我也对其抱有期待。无论如何,作者这种不人云亦云的学术勇气令人敬佩。当下中国的刑法学在犯罪论体系、分则罪名解释等方面的研究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对于方法论的反思与改进却相对不足,而“学科的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观点、体系等)的灵魂”[9],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书不仅具有知识上的价值,更具有方法论的贡献。也因此,它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为未来中国刑法学研究增添底色和路径提供了美好的图景。
【注释】
[1]参见本书第50-52页。
[2]参见本书第59-64页。
[3]参见本书第8页。
[4]参见本书第92页。
[5]参见本书第109页。这里的“当为”与“实存”,应当是借鉴了台湾学者吴从周翻译考夫曼的《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一书时所使用的术语,大体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应然”与“实然”。
[6]参见本书第171页。
[7]参见刘仁文、刘文钊:《恶势力概念流变及其司法认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21-23页。
[8]意指刑法规范内容应妥当合理。
[9]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页。
作者: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原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7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