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锴: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
王锴摘要: 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是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的例外。相对于撤销并责令重作,变更判决具有效率上的优势,避免了当事人因为行政机关不重作或者乱重作而遭受“二次伤害”。变更判决由法院来直接改变行政行为的内容也具有破坏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分工的危险。因此,变更判决的适用必须谨慎。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变更判决被限制在“行政机关没有裁量和判断余地或者裁量权收缩为零”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变更行政行为可以很好地平衡诉讼效率和权力分工之间的紧张关系。从2016年以来我国法院的83个变更判决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法院对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和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认确有错误的判断标准还存在不统一和非理性的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加强裁量基准的建设与利用诉讼调解来提高当事人对变更的接受度这两项措施加以完善。
关键词: 变更判决;裁量收缩为零;明显不当;确有错误;诉讼调解
2014年修改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新《行政诉讼法》)第77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与修改前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相比,该条在制度设计上有如下变化。首先,该条将原来条文中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改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解释,这一改动并无实质变化,[1]参只是为了跟撤销判决中的“用语”保持一致。[2]其次,该条扩大了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除了针对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外,还可以针对其他的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这主要是指涉及金钱数量的确定和认定的除行政处罚之外的其他行政行为,其中,“确定”涉及规范问题,比如行政机关在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社会保险金待遇的案件中,对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社会保险金的确定;“认定”涉及事实问题,比如拖欠税金的案件中,税务机关对企业营业额的认定。[3]自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变更判决的使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改变了过去“备而不用”的状况。[4]然而,从笔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搜集的适用变更判决的案例来看,对于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变更判决以及如何适用变更判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认识模糊之处。笔者于本文中拟从理论和司法实务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变更判决的建议。
一、变更判决的本质
一般认为,变更判决是撤销判决的例外。[5]笔者认为,这样的认知并不准确。因为撤销是否定被争议之行政行为的效力,撤销之后并没有有效的行政行为存在,而变更只是改变了原来行政行为的内容,并没有否定其效力,变更判决作出之后仍然有一个有效的行政行为存在。所以,准确地说,变更判决不是撤销判决的例外,而是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的例外。新《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一般来说,行政行为有违法和裁量瑕疵的情形,法院一撤了之即可。不过,有时法院判决撤销后,如有原告的权利义务尚需确定等情况,也就是说仅仅撤销还无法“定分止争”,则法院可以在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同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比如,行政处罚因违反法定程序被判决撤销但当事人违法行为确需予以处罚的,对当事人民事权益争议的行政裁决被撤销但该民事争议确需解决的,错误登记行为被撤销后依法应当变更登记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有错误的,等等。[6]
然而,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无讼而判”、侵犯了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违反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架空证据失权制度等等。[7]除了这些问题之外,笔者认为,责令重作判决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行政机关可能不作为,因为新《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行政机关重作行政行为设定期限;[8]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如何作出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到底是责令行政机关作为还是责令行政机关作出某种特定的行政行为,[9]新《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虽然新《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这毕竟是一种应然的要求,行政机关完全可能无视该规定而作出一个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同样,虽然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3款规定,此种情形下,法院应当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1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处理,[10]但这也反映出,责令重作判决有让当事人遭受行政机关“二次伤害”的危险。相对于责令重作判决的上述问题,变更判决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与责令重作判决相比,变更判决实际上是让法院替行政机关重作,这对于准确贯彻法院的意图、避免当事人陷入行政机关不重作以及乱重作而被迫再次起诉的“泥沼”、尽快解决争议等来说更为有利。然而,不能不看到,变更判决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法院并非行政机关,让法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本身就是个悖论。因此,变更判决既有利也有弊。相比责令重作判决,变更判决更有效率,不用担心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法院的判决,但是,与责令重作判决仍为行政机关保留了一定的裁量空间不同,变更判决直接用法院的裁量取代了行政机关的裁量,对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权力分工冲击更大。因此,变更判决能否适用的关键就在于,要在诉讼效率和权力分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必须既能发挥变更判决的效率优势又不至于危及权力分工。对此,有德国学者指出:“基于权力分工,法院原则上只能撤销行政处理(Verwaltungsakt)或者责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法院不能独立作出或者改变,或者赋予其不同的内容。但是变更判决属于例外。首先变更要有利于原告。其次,行政机关对相关的确认并没有进一步的裁量空间或者判断余地,变更判决并不要求法院用自己的裁量去取代行政机关的裁量。再次,如果原告没有申请变更行政处理,法院不能主动进行变更。”[11]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因为只有在行政机关没有裁量和判断余地或者裁量权收缩为零的情况下,即只能作出某种特定行为的情况下,由法院作出还是由行政机关作出的效果才是一样的,此时法院即使替行政机关作出也不会限制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所以,“无行政裁量和判断余地的情形或其裁量权因特殊情事而收缩为零的情形”就成为适用变更判决的最关键条件,[12]也成为新《行政诉讼法》第77条“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中判断“可不可以”的最主要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行政机关对于行政行为的作出还有裁量权,那么法院就应当选择判决责令重作而不是判决变更。
(一)无行政裁量和判断余地
区分行政裁量和判断余地是建立在区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基础上的,判断余地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问题,而行政裁量是针对法律效果的,因此也被称为效果裁量(Rechtsfolgeermessen)。行政裁量具体又可分为决定裁量(即是否产生法律效果)和选择裁量(即产生哪一种法律效果)。判断行政裁量是否存在,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方法。[13](1)法律的明确规定。比如《河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核查处理。经核查,确因进水水质和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出水水质超标的,有关部门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权时,应当将其作为从轻、减免的情形。”(2)从法律的整体规定中加以判断。比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尽管这一条并没有明确表达应作出裁量的意思,但是从“需要传唤”的表述可以看出,传唤并不是必需的,而且实践中只要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就被传唤也是不可能的。(3)通过法律的委婉说法。如果法律中使用了“能够”“可以”“有权”“授权”或者类似的表述,就表明存在裁量的空间。(4)通过应然规定。处于“能够”(裁量规定)和“必须”(羁束规定)之间的是“应当”,应然规定属于一种比较弱的裁量规定,行政机关原则上要这样做,但是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不这样做。比如我国《兵役法》第12条规定:“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该法第17条规定:“应征公民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或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不征集。”可见,在特殊情况下,兵役机关仍然有裁量权。
不确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是指一些抽象的和多义的概念,如果不通过进一步的帮助和体系性的思考,就无法单从字面获得其含义或者很难与其他概念区分,[14]比如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与秩序、必要措施、紧急情况等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属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问题,它可以分为不带判断余地的不确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 ohne Beurteilungsspielraum)和带有判断余地的不确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 mit Beurteilungsspielraum)两种。前者主要是经验性概念。[15]比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2条规定:“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处的“失效、变质”就属于不带判断余地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因为对于失效、变质的判断只能有一个答案。此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要受到法院的全面审查,法院要独立审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前提是否被满足。如果法院的判断结果与行政机关的不同,那么行政机关的决定就是违法而需要被撤销的。后者主要是价值性概念,[16]比如《学位条例》第6条第3项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此处的“创造性”就是一种主观的评价,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标准。此时法院只能进行有限的审查,即行政机关的决定在法律的框架内是否有理由。一般来说,带有判断余地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考试和与考试类似的决定。这些决定需要专业的判断,而法官缺乏这样的专业能力。然而,法院可以审查诸如考试决定是否违反程序,以及考官是否从符合实际的事实状况出发、是否考虑了不恰当的因素、是否遵守了一般的评估原则、是否恣意地作出决定等内容。其二,公职法上的能力和功绩判断。比如晋升决定、日常考核决定等。其三,如果一个决定是由免于国家干涉的、独立的、由各个方面的专家和多元的利益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作出的,则通常也存在判断余地,比如电影审查委员会、教材审定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等。其四,预测和风险决定,尤其是在环境法和经济法领域。基于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这些决定不可避免地只受有限的司法审查。其五,一些涉及行政政策、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因素,比如规划、税收中的权衡等。[17]
(二)行政裁量收缩为零(Ermessensreduzierung auf Null)
裁量收缩(Ermessensreduzierung)与裁量瑕疵(Ermessensfehler)存在着联系。裁量空间会在个案中、在特定情形下受到限制而变窄,此时作其他选择将导致裁量瑕疵。因此,裁量收缩是指在个案中裁量空间的缩小,是针对特定个案的特殊情况,且仅针对这一个案。[18]严格来说,裁量收缩为零是指选择裁量收缩为零,即只有一个法律效果可以选择。决定裁量即使收缩为零,比如行政机关有义务介入,但到底如何介入,行政机关在手段上仍有裁量空间。
造成裁量收缩为零的因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19]这种内在因素首先来自于裁量规范的目的,即立法者为什么要在调整这种事实时联结一个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裁量规范的目的越重大,裁量也就越容易收缩为零。比如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越严重,警察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重大性一方面通过其保护的法益的重要性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个案中法益具体受到侵害的程度。这种内在因素其次要考虑与裁量规范处于相同位阶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也会对裁量收缩产生影响。有人可能说这种影响是来自于外部的,属于裁量收缩的外在因素,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必须与裁量规范之间存在事务上的联系,比如建筑法上的邻人保护条款会对有关拆除建筑物的裁量决定产生影响。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这种内在因素还包括利益衡量。裁量权的行使往往就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一方的重要性压倒了另一方并且另一方没有更多的理由存在,那么,就会导致裁量收缩为零。这种外在因素主要来自于裁量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基本权利、比例原则和行政的自我约束。首先,基本权利对裁量权行使的影响来自于宪法对行政法的约束力,因此基本权利主要是作为裁量空间的客观界限而存在的。比如决定裁量通常以作为义务的存在为前提,这又与基本权利作为受益权或者分享权以及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有关。其次,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决定采取某项干预或者保护基本权利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只有这样才不会侵犯基本权利。如果选择其他的行政措施都不合比例,那么此时裁量就会收缩为零。再次,行政自我拘束。第一,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承诺(Zusage)、保证(Zusicherung)或者公民值得保护的信赖来形成自我拘束。第二,行政机关通过平等原则来形成自我拘束,即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行政机关不能改变先前的行政实践,而是说不能恣意地改变。即使在改变的情况下,也可能基于信赖保护导致裁量收缩为零。
在特定的情况下,裁量收缩的因素会被排除,其包括以下几种情况。[20]第一,行政机关虽然基于裁量收缩而有义务作出某种行为,但这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警察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第二,不具有可期待性。可期待性主要是从个案的角度对抽象的手段与目的权衡的纠正。比如轮岗对于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干预是妥当的、必要的和合比例的,但是基于重大的个人或者家庭的理由,对于个别情况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比如,某公务员的妻子是需要透析的病人,如果其到了新的工作地点,则其无法照顾其妻子或者照顾其妻子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21]第三,丧失权利。比如,一个要求行政机关干预的请求权因为没有及时行使而丧失,此时行政机关将从作为义务中解脱出来。第四,辅助性原则。比如根据《信访条例》第14条第2款和第21条第1款,信访机关受理信访的前提是该争议无法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此时,信访行为的作出不具有优先性。
二、行政处罚明显不当[22]
(一)明显不当的内涵
在行政法上,明显不当属于裁量瑕疵的问题,即属于不合理的范畴。[23]从字面来看,明显不当就是明显不合理,[24]与明显不当相对应的是一般不当(一般不合理)。然而,实际上,在行政诉讼中区分明显不当与一般不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法院审查能力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所能审查的是明显不当,对于一般不当应交给行政复议去审查,这也是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区别之一。比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第1款规定:“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果房屋出租人的违法行为较轻,应当被给予210元罚款,而行政机关处罚了499元,那么属于明显不当,这也就是所谓的“畸重畸轻”,此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依靠一般人的常识就可以判断。相反,如果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当被给予210元罚款,而行政机关处罚了220元,这就属于一般不当。对于一般不当,必须依靠长期的行政经验才能判断。因为在行政处罚中,到底针对何种情况应当给予何种程度的处罚,即裁量基准,是长期的处罚实践积累的结果。法官由于不从事处罚业务,难以体会其中的尺度拿捏,因此也就无法期待法院能够审查一般不当问题。相反,行政复议机关作为被申请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其专业知识和资历(即行政经验的丰富)都要胜过下级行政机关,这也就是行政复议既能审查合法性又能审查合理性的原因。因此,对于法院来说,裁量瑕疵就意味着明显不当。裁量瑕疵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25](1)裁量怠惰(Ermessensnichtgebrauch、Ermessensunterschreitung)。裁量怠惰就是行政机关不行使裁量权,尽管法律规定其应当裁量。比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第1款要求公安机关根据房屋出租人违法行为的情节,给予200元至500元的罚款。如果公安机关对于任何有上述违法行为的房屋出租人都一律给予499元的罚款,就属于裁量怠惰。(2)裁量错误(Ermessensfehlgebrauch)。裁量错误具体又包括以下四种情形。第一,目的错误,即行政机关没有注意或者没有充分注意法律规定的裁量目的。比如公安机关对于“有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没有逃避传唤的人”进行强制传唤,这就不符合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的强制传唤的目的。第二,权衡不足,即行政机关在权衡中没有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比如行政机关在作行政处罚时,没有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第三,侵犯基本权利和一般的法律原则。基本权利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提出要求或者作出禁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裁量要考虑的因素。一般的法律原则包括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等。第四。没有考虑裁量权收缩为零。比如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62条规定:“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以及其他依法配备、携带武器的应对处置人员,对在现场持枪支、刀具等凶器或者使用其他危险方法,正在或者准备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紧急情况下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可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武器的裁量权发生了收缩。德国学者通常还将裁量逾越(Ermessensüberschreitung)作为裁量瑕疵。[26]裁量逾越是指行政机关的决定处于法律设定的法律后果框架之外,[27]比如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罚款50元至100元,而行政机关最终处罚了40元或者200元,这就属于裁量逾越。这种认识的问题在于,裁量逾越既然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幅度,就已经不属于不合理的问题,而属于不合法的问题。这与裁量瑕疵整体上定位于不合理是冲突的。因此,笔者更愿意将裁量滥用(Ermessensmissbrauch)作为裁量瑕疵的一种独立形态,对应于我国的滥用职权。只不过,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区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其中滥用职权侧重于主观的不合理,而明显不当侧重于客观的不合理,[28]所以裁量滥用这种裁量瑕疵并不属于明显不当的范畴。
(二)变更判决中对“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判断标准
笔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搜集了2016年以来的83个作出变更判决的案例,其中有60个案例是涉及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占全部案例的72%。通过分析这些案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院判断“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标准。(1)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明显不当”是因为处罚机关没有考虑行政处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所导致的。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的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是相同的,实践中对两者的使用存在随意性。[29]相对于“从轻”有法定最低幅度的限制,“减轻”是在法定幅度之下进行减少,减到什么程度,法院享有巨大的裁量权,特别在“拘留并处罚款”的减轻中,有的法院减为拘留,有的法院减为罚款,很不统一。[30](2)一些“明显不当”是由处罚机关适用法条错误引起的,比如在“柴允与商水县公安局治安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6)豫16行终221号]中,“被告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而适用了第23条第2款”,导致处罚畸重。还有一些“明显不当”是对法条的解释错误引起的,比如在“佛山市南海区君诺电子厂与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之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7)粤06行终610号]中,法院指出:“《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中的‘每月’应指使用天数,而非南海人社局理解的自然月。本案中,君诺电子厂于2016年7月26日开始使用周某工作至2016年8月2日,不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南海人社局应按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但南海人社局的处罚计算标准中,按7月和8月两个月计算,是对上述规定的理解错误。对君诺电子厂处10000元罚款,处罚数额明显不当。”另有一些“明显不当”是由行政机关的证据不足导致的,比如在“孙凌文与舒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疗行政处罚一案再审行政判决”[(2018)吉02行再2号]中,法院认为:“舒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认定孙凌文系伪造医学文书证据不充分,适用情节严重予以吊销执业证书处罚过重,明显不当。”这些情形之所以都被归入“明显不当”,原因在于我国法院对“明显不当”的判断并没有坚守合理性审查的立场。[31]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来看,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撤销判决或者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的情形,对其适用变更判决是有问题的。(3)个别案例使用了比例原则来论证处罚的明显不当,比如在“胡以锋与淄博市周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7)鲁03行终212号]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罚款30000元的处罚决定超过了其行使行政管理措施的必要性,手段和目的不具有相称性,对上诉人的侵害明显大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的获益。”(4)个别案例使用了裁量基准来说明处罚的明显不当并确定适当的处罚。比如在“庞志鑫与日照市岚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7)鲁11行终70号]中,法院认为,根据《山东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13条“减轻行政处罚不得低于法定裁量幅度最低倍数或数额的10%”的规定,可以将罚款幅度降至最低幅度进行裁量,那样处罚将更为适当。(5)个别案例对比了同案中行政机关对其他人的处罚来说明某项处罚的明显不当,这相当于使用了行政自我拘束来限缩裁量空间。比如在“延吉市林业局诉金淳吉林业行政处罚一审行政裁定”[(2018)吉2401行审49号]中,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在同一事实上对他人(孙杰、金都成)的处罚是每平方米5元标准处以罚款,但对本案的被执行人是每平方米10元标准处以罚款,违反了行政处罚应当遵循的公正公平原则。”
总体而言,我国法院在对行政处罚明显不当进行变更时存在不统一和非理性的问题。其一,大多数法院即使能够证明原处罚明显不合理,但无法提出为什么自己变更后的处罚就是“唯一合理”的(一些法院在判决中坦承它们变更后的处罚只是“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对于适用变更判决的最关键要件,即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的选择上是否裁量权收缩为零,大多数判决缺乏论证。
其二,从“不当”的明显程度上来看,各地法院的认识参差不齐。通过对比变更后的处罚与变更前的处罚的差距可知,最多的可以相差50倍,比如在“仙居县徐苏珍蔬菜商行与仙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二审行政判决”[(2017)浙10行终110号]中,原来罚款5万元,变更后罚款1千元。当然如果是跨处罚种类变更,差距就更大了,比如在“青岛天地缘网吧与青岛市崂山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文化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7)鲁02行终850号]中,法院将原来的处罚“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变更为“责令停业整顿30日,并处1万元罚款”。最少的相差不到一倍,比如在“刘楠与涟源市公安局、娄底市公安局、第三人谢红日治安行政处罚一审行政判决”[(2017)湘1382行初108号]中,法院将原来的拘留五日改为拘留三日。对于这种不到一倍的处罚差距,能否说明原处罚明显不当,颇有疑问。
三、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
(一)款额确认“确有错误”的判断标准
如前所述,将变更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是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情形。该条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2款类似。后者规定,如果原告要求改变行政处理(Verwaltungsakt)所确定的金额或者一个与此相关的确认,法院可以将其确定为另一数额或者用另一个确认来取代原有确认。如果为确定或确认金额所进行的调查需要花费巨大,法院可以在指明未被正确考虑或未被考虑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前提下,指定由行政机关基于上述理由计算出金额。行政机关应当立即将新的计算结果通知当事人,此通知的形式不限。裁判生效之后,被变更后的行政处理应当重新公布。在德国,变更判决主要针对涉及金钱给付的行政处理,包括规费、罚款、保险费以及对补偿费用或者公法上的支出的确认等等。这一点与我国法规定的“行政行为对款额的确定、认定” 是相同的。其不同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法表面上并未要求行政机关对款额的确认确有错误,但实际上变更判决是作为撤销判决的“前置程序”而存在的,即撤销一个金钱给付的行政处理是在无法变更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撤销判决的可允许性对变更判决也是适用的。[32]第二,德国法规定在法院变更不方便的情况下(确定或确认金额所进行的调查花费较大),可以让行政机关自己变更。这主要是考虑到那种大规模的计算,行政机关更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33]当然,行政机关的计算仍然要在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即在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争议已经被法院澄清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仅仅是进行数据运算而已,这可以避免行政机关自己变更违背法院的意志。必须注意的是,上述变更都是在行政机关没有裁量空间和判断余地的情况下进行的。[34]
“确有错误”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确有错误”是指行政处理的“显然错误(offenbare Unrichtigkeit)”,即行政处理因为书写错误、计算错误、疏漏或者自动化作业的错误等导致其所表现的内容与行政机关的意思不一致。因为显然错误在客观上一望可知,即应如何改为正确十分明白。因此行政机关可以随时更正,并且不需要考虑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和法律安定。[35]从笔者搜集的案例来看,在“曾英与资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一审行政判决”[(2017)川1025行初23号]中,法院就指出:“被告在录入相关信息时,由于操作失误,导致合伙人出资情况一项中原告曾英与第三人傅一勋的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比例的登记与该企业申报的内容不符。”据此,法院最终变更了合伙人出资情况登记中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广义的“确有错误”应当包含所有导致行政行为款额确认错误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事实不清。比如,在“戴祖唐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案”[(2016)沪02行初392号]中,法院变更征收补偿款的原因是“被告认定该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有误”;在“王万录不服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一案一审行政判决”[(2017)辽09行初40号]中,法院变更的原因是“补偿项目有遗漏”;在“李添源与鹤山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管理一审行政判决”[(2017)粤0704行初137号]中,法院变更的原因是“江门市正恒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宗地作出的《土地估价报告书》的估价日期与涉案《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作出时间不一致”。第二,适用法律错误。比如在“刘芳与高青县居民养老保险事业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8)鲁03行终89号]中,法院责令被告变更养老金月发放标准,理由是“被告的标准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第五条规定”。前述两种“确有错误”类型正好分别对应于认定错误和确定错误。笔者认为,狭义的确有错误更符合变更判决的本义,因为在款额因为计算、书写而显然错误的情况下,无论是行政机关变更还是法院变更,变更后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改为原来正确的数字。然而,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广义的认定错误和确定错误,还是必须限定在行政机关对款额的认定、确定没有裁量和判断余地或者裁量权收缩为零的情形。
(二)变更判决中涉及款额确认错误的案例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笔者搜集的83个作出变更判决的案例中,涉及款额确认的案例有23个,仅占所有案例的28%,而且其中80%以上的案例是关于征收补偿款的确认。目前涉及款额确认的变更判决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些法院的变更缺乏实质性的理由,即没有指出原来行政机关的款额确认“确有错误”(见表1),而是基于“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补偿方案”,甚至是“为了减少诉累、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等政策性的考虑。这就使得款额确认的变更判决成为无原则的“和稀泥”。比如,在“沈云龙因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上诉案”[(2017)沪02行终122号]中,法院变更了对原告的征收补偿款,原因为“对原告的房屋性质认定有误”,但是从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行政机关认定有误的实际原因竟然是“原告明知其于2010年11月即在涉案房屋内注册有营业执照,但在征收过程中,未向征地事务机构释明,其自身存在过错”,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款额确认“错误”是原告的过错引起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进行变更,则显然违背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变更判决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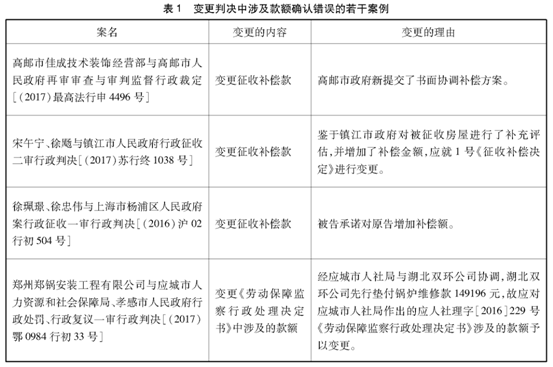
表1变更判决中涉及款额确认错误的若干案例案名变更的内容变更的理由高邮市佳成技术装饰经营部与高邮市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2017)最高法行申4496号]变更征收补偿款高邮市政府新提交了书面协调补偿方案。宋午宁、徐飏与镇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二审行政判决[(2017)苏行终1038号]变更征收补偿款鉴于镇江市政府对被征收房屋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增加了补偿金额,应就1号《征收补偿决定》进行变更。徐珮璟、徐忠伟与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案行政征收一审行政判决[(2016)沪02行初504号]变更征收补偿款被告承诺对原告增加补偿额。郑州郑锅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应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孝感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审行政判决[(2017)鄂0984行初33号]变更《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涉及的款额经应城市人社局与湖北双环公司协调,湖北双环公司先行垫付锅炉维修款149196元,故应对应城市人社局作出的应人社理字[2016]22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涉及的款额予以变更。安顺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与贵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税务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2017)黔04行终27号]变更《税务处理决定书》中的应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以及少缴税款及滞纳金的缴纳方式为了全案的妥善处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王森林与镇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2017)苏行终472号]变更征收补偿款对于王森林请求分户安置的请求,经协调,句容市政府同意分户安置。句容市政府征收实施单位自愿参照该项目协商征收的情况,增加对涉案房屋、装修、附属物等补偿,并且提供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套方案。故原审法院对此承诺予以采纳。
四、结论
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既要让司法权能够有效监督行政权,又要维护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分工。变更判决是行政诉讼中对权力分工冲击最大的判决类型,因此法院在适用时必须谨慎,应当坚守“只有没有行政裁量或者判断余地以及行政裁量收缩为零,才能用法院直接变更行政行为来代替行政行为重作行政行为”的原则。否则,不仅会导致司法裁量取代行政裁量的后果,而且会赋予法院过度的裁量权,甚至可能引发司法腐败。这在一些款额巨大的变更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安顺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与贵州金星啤酒有限公司税务行政管理二审行政判决”中,法院将金星公司的应缴税款从2163万变更为803万,减少了1300多万。有鉴于此,从控制司法裁量权和避免滥用变更判决的角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变更判决的适用。一方面,进一步加强裁量基准的建设,实践证明,裁量基准对于合理性审查的精细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法院排除不合理的裁量,而且有助于法院确定合理的裁量。另一方面,在目前尚未将“行政机关没有裁量和判断余地收缩为零”作为变更判决的实质要件的情况下,利用诉讼调解制度来提高争议双方对变更判决的接受度。我国法院对变更判决的理由缺乏精细论证的现状会导致争议双方对法院的变更都不满意的后果,从而使变更判决的效率优势无法发挥,甚至陷入循环诉讼(比如在60个涉及行政处罚的变更判决中,一审只占31.6%)。新《行政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该法也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这使得绝大多数变更判决可以同时适用诉讼调解(由于计算、书写等错误导致行政机关对款额的确认显然错误的行为是例外,因为此时行政机关没有裁量权),此时,法院可以通过调解来促成双方在处罚幅度以及金钱给付款额上的“合意”,诉讼调解书将发挥变更原来行政行为的作用,而建立在这种三方合意基础上的变更更能获得当事人的认可。实际上,在笔者搜集到的案例(主要是涉及款额确认的案例)中,已经有法院将自己的变更建立在非正式的“协调”上了。[36]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ories and Cases
Wang Kai
Abstract: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is an exception to revoking the original administrative act and ordering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to make a new act.
Compared with the later, the former has the advantage of efficiency and economy, and avoids “secondary injury” suffered by the Parties due to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failure to make a new action or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wrongful new action. The fact that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allows the court to directly change the cont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has the risk of impairing the division of power between judicial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refore, the court must be cautious in applying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rom the situations of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is limited to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has no discretion and judgment space or the discretion shrunk to zero.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courts can change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to balance the tension between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division of power. From 83 cases involving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of the Chinese courts since 2016,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still inconsistencies and irrationalities in standards for the court to determine that a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s obviously improper and an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volving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amount of money is really incorrect. In the future, such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nd the system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wo measures: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cretionary benchmarks and utilizing litigotiation to improve parties’ acceptance of the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Keywords: Judgment of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Discretion Shrunk to Zero; Obviously Improper; Really Incorrect; Litigotiation
注释:
[1] 参见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页。
[2] 参见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2页。
[3] 参见前注①,信春鹰书,第203页。
[4] 在实践中,有法院突破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7条规定的两种情形,比如在“陈健与淄博市临淄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分处、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一审行政判决”[(2017)鲁0305行初39号]中,法院变更了将养老金纳入社会统筹的日期;在“徐志高与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治安管理一审行政判决”[(2017)赣0602行初20号]中,法院将强制隔离戒毒的行政强制措施变更为在社区戒毒。
[5]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19页。
[6] 参见前注①,信春鹰书,第190页。
[7] 参见刘欣琦:《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重作判决适用探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
[8] 参见张林:《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期限问题》,《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0条第1款规定,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如不及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的,可以限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这一司法解释目前已失效。
[9] 参见项一丛:《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法理分析》,载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公法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法院审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案件,认为原告请求准予许可的理由成立,且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可以在判决理由中写明,并判决撤销不予许可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然而,这种情形到底是用履行判决还是用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尚值得讨论。因为我国一般将行政不作为理解为行政机关没有任何作为,才会出现该条中对于行政机关不予许可的决定先撤销再责令许可的规定,但实际上,行政不作为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机关有没有作为,而在于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作为义务,因为不予答复(没有动作)和拒绝作为(有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行政机关不予答复和拒绝作为实际上都属于不作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行政机关应当许可而不予许可的情形,法院直接判决履行即可,用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反而显得繁琐。对此,201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已经纠正。
[10] 实践中,有法院针对行政机关重作时又作出跟原行为基本相同的行为,采用直接变更的方式来救济,比如,在“王遵虎与襄阳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处道路交通管理一审行政判决”[(2017)鄂0606行初156号]中,法院指出:“本院在2017年9月5日作出的(2017)鄂0606行初119号行政判决已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依然作出处罚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3款的规定。
[11] Heinrich Amadeus Wolff & Andreas Deck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und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Studienkommentar, 3. Aufl.,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12, S. 441-442.
[12] 陈清秀:《行政诉讼法》(修订七版),元照出版公司(台北)2015年版,第651页。
[13] Steffen Detterbeck,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15. Aufl., C.H.Beck, München, 2017, S. 95-96; Franz-Joseph Peine,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0. 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 49-50.
[14] Hans Peter Bull & Veith Mehde,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it Verwaltungslehre, 8. 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 241.
[15] 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16] 参见上注,王贵松书,第62-63页。
[17]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srecht, 18. Aufl.,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11, S. 158-159; Ulrich Batti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3. 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2, S. 150-152.
[18]参见[德]卡尔-埃博哈特·海因、福尔克·施莱特、托马斯·施米茨:《裁量与裁量收缩——一个宪法、行政法结合部问题》,曾韬译,《财经法学》2017年第4期。
[19] Vgl. Karin Laub, Die Ermessensreduzierung in der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Rechtsprechung, Herbert Utz Verlag, München, 2000, S. 32-40.
[20] a.a.O., S. 45-46.
[21] Detlef Merten, Verh?ltnism?βigkeitsgrundsatz,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 559-560.
[22] 有学者对变更判决能否适用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提出质疑,理由是“如果处罚行为效力丧失或者执行完毕后,就无法简单地通过撤销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因此,也无法适用变更判决”。参见张峰振:《论不当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从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明显不当行政行为”谈起》,《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的确,对于已经丧失效力或者执行完毕的自由罚、名誉罚、行为罚进行变更会存在变更后执行难的问题,比如原来拘留10日的处罚已经执行完毕,即使法院变更为拘留5日,又如何消除已经被多执行5日的后果呢?然而,
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变更判决不适用于行政处罚的理由。首先,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中增加“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但不具有可变更内容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来弥补;其次,即使变更后导致的处罚减少因执行完毕而没有使被处罚人享受到减少的好处,但这可以通过国家赔偿来救济,也就是说,法院的变更判决可以作为当事人就额外承受的处罚请求国家赔偿的依据;再次,因为处罚被执行完毕而导致变更失去意义的根源在于我国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如果因此而取消变更判决对行政处罚的适用是“因噎废食”。
[23] 当然,从实质合法的角度看(即合法并不限于符合成文的法律规定,还包括符合不成文的法理、原则等),“明显不当”也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合法性审查的范畴。参见何海波:《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4] 参见前注②,江必新、梁凤云书,第1611-1612页。
[25] 参见前注, Detterbeck, S. 98-101.
[26] J?rn Ip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8. Aufl.,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2, S. 132; 前注, Bull & Mehde, S. 255-256;前注, Battis, S. 142.
[27] 参见前注, Detterbeck, S. 99.
[28] 参见前注①,信春鹰书,第190页。
[29] 比如同样因为违法行为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李育鑫和青州市公安局治安一审行政判决”[(2017)鲁0781行初96号]中,法院将原处罚“拘留五日并处罚款200元”减轻为“罚款400元”;在“朱某与商城县公安局、商城县人民政府治安管理一审行政判决”[(2017)豫1522行初14号]中,法院将原处罚“拘留十二日并处罚款700元”从轻为“拘留三日并处罚款200元”。
[30] 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4条第3项、第4项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具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减轻处罚情节的,按下列规定适用:……(三)规定拘留并处罚款的,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单独或者同时减轻拘留和罚款,或者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单处拘留;(四)规定拘留可以并处罚款的,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减轻处罚;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然而,在实践中该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守,一些法院经常将“拘留并处罚款”减轻为罚款。
[31] 参见于洋:《明显不当审查标准的内涵与适用——以〈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六)项为核心》,《交大法学》2017年第3期。
[32] Ferninand O. Kopp/ Wolf-Rüdiger Schenke/Ralf Peter Schenke,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Kommentar, 19. Aufl., C.H.Beck, München, 2013, S. 1392.
[33] Andreas Decker, §113, in: Herbert Posser & Heinrich Amadeus Wolff (Hrsg.), VwGO Kommentar, 2. Aufl., C.H.Beck, München, 2014, S. 840.
[34] a.a.O., S. 840.
[35] 陈敏:《行政法总论》(第九版),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16年版,第386页。
[36] 比如,王森林与镇江市人民政府行政征收、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2017)苏行终472号];郑州郑锅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应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孝感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一审行政判决[(2017)鄂0984行初33号];高邮市佳成技术装饰经营部与高邮市人民政府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2017年)最高法行申4496号]。
作者简介: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9期。

